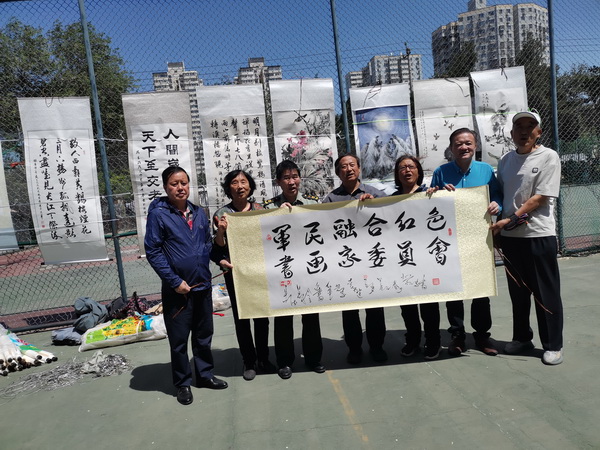|
第一条道路 政府主导、农民被动 总体描述:以政府征用农地、出让土地、抵押融资来推动城市化,政府成为投资主体、利益主体、建设主体,效率高,但成本巨大。有城市没有人,有政府没市场,农民利益受损,群体性事件频发。 新京报:为什么要寻找中国城市化第三条道路? 刘守英:目前已经有两条道路了,第一条就是目前所实行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加速推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,我称之为“政府主导、农民被动”,政府是城市规划的主体、建设的主体、基础设施投资的主体、GDP主要的渴求者和创造者,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城市外观非常漂亮、发展非常迅速。 新京报:为什么这条道路可以实现城市化的迅速推进? 刘守英:这是整个国家土地制度导致的结果。 一是利用城乡土地二元结构,政府从农民那里按照原产值低价征收土地,再高价卖出土地,价差使政府成为土地利益的获得者; 二是政府利用规划权不断扩张城市,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,再将土地抵押获得贷款,城市基础设施建设70%资金都来自于土地抵押贷款,大家关注更多的所谓“土地出让收入”,其实只抵消了土地抵押贷款的利息。 三是城市利用低价征来的土地,招商引资,发展工业园区,政府获得税收收入。 通过这些方式,政府获得了城市建设的资金。土地就是发动机,启动了整个城市投资和建设,物质形态的城市发展非常快,这可以称为“中国城市化的秘密”。 新京报:这种模式存在哪些弊病呢? 刘守英:一是金融风险。抵押土地获得银行资金支持,是预支未来的城市化,比如预期某块地将盖成商业楼盘,可能值多少钱,银行按照评估价的75%提供贷款,但是,如果发展的不如预期,资金就会出问题。而且贷款以财政做担保,财政靠国库里的钱,这也有风险。 二是农民利益受损,因为他只获得了按照原土地用途的补偿,不是利益的分享者,他就会想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卖地或开发房地产,结果就是小产权房问题以及上访等。 三是整个城市化不解决人的问题,“城中村”就是典型。政府虽然通过征地将土地迅速城市化,但城市化核心是人的城市化、人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,把“农民”变成城市形态的“市民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,而是一场革命,一场生活方式、价值观、产业形态的革命。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只有土地没有人。 新京报:这条路还能继续走下去吗? 刘守英:我们承认这条路的好处,它带来的城市化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,不可抹杀,但必须看到,这条路已越来越难走了,有两大成本必须考虑: 一是住房成本,土地垄断的模式导致资源稀缺,要素市场扭曲,推高了整个住房的成本,引起居民不满;二是农民不满的成本,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,而且在不断累积。 政府现在是两头不落好,获得土地时得罪农民,终端又得罪买房的人,被骂唯利是图。 新京报:确实是这样。 刘守英:其实,政府并不是利润最大化者,除了某些官员可以获得腐败机会,政府要那么多钱干吗?最终还是用来建设城市。 城市土地只有15%-20%是可卖的,工业用地是按照成本价供应的,其他土地都是划拨的,后者占大头,用商业化的土地收入来平衡80%没有收入的土地的建设成本,大多数城市是平衡不了的。 既然如此,就必须考虑,政府搞这样的城市化干什么,图什么! 第二条道路 政府退出,农民自主自发 总体描述:政府充当“旁观者”,完全由农民自主自发推动城市化,虽然解决了农民收益问题和城市流动人口居住问题,但产生了严重城市病,属于无序的、混乱的、法外的城市化,不可持续。 新京报:第二条道路是什么样的? 刘守英:第二条道路是农民完全自主自发的城市化,这条路现在也在走,表现为两种形态。 第一种是城中村,当政府将他们的大部分土地征用、抵押、出让时,农民自己也在利用剩余的土地毫无规划地参与城市化,分享土地级差收益,他们自己盖了很多高楼,通过出租获得收入,解决了城市政府措手不及的大量涌入的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。 他们的贡献不容抹杀,要知道,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其实是不装人的,能买得起几万块一平米房子的毕竟不是多数,大多数人是流向了价格低廉的城中村,北京700万流动人口,80%在城中村。 第二种是在城市圈子外的农民靠产业化发展聚集人口,从产业非农化到人口非农化的模式,像北京的郑各庄。它的好处是,农民靠房租和产业,解决了收入问题,分享了土地级差收益。 新京报:这条道路不好吗,至少农民享受了城市化的好处? 刘守英:从农民获利的角度看,它确实好。但是,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,城市化决不能是原子式的市场化,它必须是有规划、有功能分区的,财富的积累必须是有法律保障的。没有秩序、没有规划的城市化,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可收拾的,也完全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城市化。没有法律保障的城市化,当事人也没有好的长远预期。 新京报:为什么? 刘守英:先说城中村,农民除了增加了收入,没有任何城市的幸福感,犯罪、安全、消防等问题非常大,管理成本极高,虽然我们不承认它是贫民窟,但这不就是典型的城市病吗?政府觉得是隐患,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不觉得幸福,严格说起来,是与城市化不相容的。 再说圈外农民在集体土地上长出来的城市,第一,整个制度不接纳,法律规定圈内叫城,圈外叫村,你有什么权力建城市?第二,集体土地,只能长苞谷或自己搞乡镇企业,怎么能长城市,谁让你建住宅楼了,谁允许你卖了?第三,无论圈内圈外,都是在不符合规划的情况下长出来的,基础设施与城市两张皮,设施立项不批准,建设立项不批准,是法外经济,法外的城市化;第四,治理结构上没有当做城市对待,你房子盖的再漂亮,身份仍然是农民,按照农村的治理结构治理,与城市无法对接;第五,村庄腐败,权力、资金、能力大的人多占,无公平可言。 总体而言,这条农民自发的城市化模式,将城乡二元体制隔离表现的淋漓尽致,而且强化了这种隔离。 第三条道路 规划主导、农民主体 总体描述: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组织者、服务者、制度提供者,主动破解二元体制藩篱,对规划、土地、资金、基础设施、社保、人口管理等主动改革,允许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土地市场。 新京报:第三条道路是怎么设计的? 刘守英:第三条道路是妥协的道路,最好的方案是“规划主导、农民主体”,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“政府主导、农民主体”,目前只能选择第二个方案,逐步走向第一个方案。 新京报:能否具体谈谈? 刘守英:最好的方案是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把第二条道路合法化,现在的规划是“用途管制+所有制管制”,农地转非农要审批,集体转国有要审批,但由于政府可以随意调整规划,只要占补平衡,就可以征收农地,用途管制形同虚设。 其实,规划管制最根本目的是功能管制,只要空间符合规划,不管集体还是国有,都可以平等进入市场,集体土地拥有平等的建设、立项、发展产业的权利,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级差收益。 这就是“规划主导、农民主体”,简单说就是政府完全作为规划者,土地让农民自己去开发。 新京报:这个方案不可行吗,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地走“政府主导、农民主体”? 刘守英:首先是规划能不能硬起来,目前还是行政权大于规划权,我们担心目前还做不到;第二,基础设施建设,一个村是做不起来的,必须由政府主导来做;第三,社会保障体系同样需要政府来主导;第四,更主要的,我们目前这套二元体制把农民排斥在外,政府不主动来破,农民自己是挣脱不掉的。 所以,我们设想走一条“政府主导、农民主体”的道路,有几个核心意思: 一、政府不再充当土地经营者,而是作为城市建设的组织者、服务者、制度提供者,政府主动在规划、土地、立项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破解城乡二元体制,打开农民参与城市化的合法大门。 二、将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完全用于解决这一地区的城市化问题,即在城市一体化规划下,完全用于解决农民的居住、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,促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。简单说,就是政府拿一部分地到市场上卖,这个钱完全用于解决这一块土地上的城市化问题,平衡就行,不能谋利。而第一条道路中政府是要把土地盈余做到最大化的,这个方案解决了第一条道路的弊病。 三、要为农民留产业用地。过去农民上楼就不管了,只有土地的城市化没有人的城市化,现在要给农民留一块地,用来发展城市产业,让农民长期分红。毕竟城市化是极长期的生活方式的转型,如果一下子断掉,给多少钱都不行,要留一个产业,让他有一个长久的过渡。像北京在集体土地上搞公租房,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。这里的关键是,解决规划和用途管制下,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平等进入问题,真正实现两种土地所有制的“同地、同价、同权”。 新京报:有个问题,之前提到,政府需要很大的资金去搞协议转让等地区的城市化建设,如果无法通过征收农地盈利,这部分钱怎么解决? 刘守英:第一,我们到底要不要做那么多的公共目的用地,建那么多的广场、马路,政府盖那么多楼?第二,工业用地不能再低价协议转让了,要靠市场来做。 在这些供地结构改变后,就不需要那么多钱了。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赵继成 中国规划网北京12月4日电 (责任编辑:白雪松) |